编者按:这是唐丹鸿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加沙战争手记。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当人们撕下人质招贴的影像映入我眼帘时,我想起了多年前,家人的故交博伊特(Brurit)打来电话,邀我们参加一个她组织的和平活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起献血。这些血液将混在一起,输给无论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博伊特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父亲在以色列独立前被阿拉伯人杀了。带着这些略感古怪的记忆,我去拜访了博伊特。
1.无边界
“我母亲巴哈尔(Bracha)出生在波兰,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她姐姐是一位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钢琴家。她哥哥是波兰设计师协会体育部主任。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在与德国相邻的波兰城市,开了波兰首家罐装鱼工厂。我外公非常热衷艺术,有很多艺术收藏。许多艺术家是家里的宾客。这是一个文艺氛围浓郁的家庭。我母亲也有这种特质。这就是后来她成为了策展人、家有很多艺术藏品的因源。
我母亲的哥哥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先到以色列,当时叫巴勒斯坦。受哥哥影响,1938年我母亲19岁时也到了这里。他们曾恳求父母和姐姐同来以色列。她父亲说我们是波兰人。无论波兰发生什么我们都会留在这里。其实,由于我外祖父是商人,他有特别证书赋予的特权,能自由离开波兰。他本可以解救自己,但他非常爱妻子。他试图营救妻子和大女儿,没有成功。没有她们,他也不想活了。于是他与她们一起去了集中营。不知在集中营他是否见到过她们,因为集中营里男人与女人是分开的。
那时已有不少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基布兹 (kibbutz)。我母亲希望加入一个蕴含文化的基布兹。于是她找到了我父亲所在的基布兹。我父亲本尼是一位诗人,多才多艺。他写诗在聚会上朗诵,还写故事和剧本。他创作了以色列第一部音乐剧,由萨沙·阿尔戈夫作曲,在以色列多地演出,我父亲也在剧中演出。我母亲在基布兹办了一个托儿所,做了六个孩子的保育员。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本尼受她影响,成了以色列第一位男保育员。
本尼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的左翼文章。基布兹里所有人都关注和参与政治。他们非常理想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灵性的方式看待现实。本尼的父亲、也即我祖父,过去常常带他去内盖夫沙漠的基布兹古洛特(Gulot)旅行。希伯来语‘古洛特’的意思是‘边界’。他们去‘边界’骑马。那里靠近贝都因人的地方,古洛特基布兹的人与那些贝都因人关系很好。我父亲写了一首关于那儿的诗,诗名叫《无边界》(No Borders)。他认为边界并不真实,而是人为虚构的。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短诗。基布兹的名字古洛特表达人们对于以色列边界的设想,而大自然是没有边界的。
2.明晰的诗
1947年,我一岁生日的前几天。本尼去特拉维夫为托儿所的孩子们买玩具。当时正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暴力冲突时期。他父母劝阻他不要去,我祖母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父亲还是去了。他搭乘了基布兹的一辆车前往特拉维夫。在快到雅法(Jaffa)的时候,有一群阿拉伯人堵在路上,朝车投掷石头和射击。司机受了伤,车停了下来。车里其他几个人都躲在车里。我父亲,也许他以为能够逃脱,也许他想去求援。总之他是唯一一个跑出车去的人。这群袭击者追上了他,用刀划开了他的喉咙。英国警察很快赶到了,待在车里的所有人都得救了。本尼被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他那时29岁。
在那段暴力时期中,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尔贡,杀害了一些阿拉伯人。我父亲被杀是阿拉伯人对那些杀戮的报复。实际上,我祖父的兄弟是伊尔贡的负责人,非常右翼。而我父亲的基布兹属于一个最左翼的组织。他与这位右翼叔叔有很多政治争论。
花了很多年时间,我母亲才开口跟我谈论父亲。她说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当她父母被纳粹杀害时,她也有过这种感觉。她走到屋前的一棵树下,坐在那里等待人们带来本尼的死讯。人们来告诉她本尼死了。也许真相太震撼了,他们给了她一个不太真实的故事。他们说本尼从车里出去试图与阿拉伯人沟通对话,被阿拉伯人枪杀了。她一直相信这个故事。这也是我成长过程中被告知的版本。直到母亲已经相当老的时候,我才从我祖父的兄弟那里获知真相。而我母亲从不知道。
本尼被杀后,母亲没有参加葬礼。她把我托给她哥嫂,自己去另一个基布兹待了几天。我从未理解她为何没有带我一起去,但她说她不能,她处于震惊状态。那时的人崇尚坚强,你不能哭泣,不能表露情感。我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带着我到了特拉维夫。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察夫塔(Tzavta)文化中心的第一任主任。195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察夫塔被视为以色列艺术家和作家的故乡。
我母亲常在夜晚工作。家附近有一所学校,有些孩子很亲近我母亲,有时她们来帮忙照料我。我们住在一座小丘上的村子里,可以步行到海边。我觉得那是一个有魔法的地方,常常练习集中意念,以为只要足够专注,我就能飞起来。那里风景很美,有美丽的花朵、仙人掌,有大海。
母亲几乎不和我谈父亲,更不说他是如何死的。可能她太伤心了。儿时的我脑中充满了父亲如何去世的幻想。所以八岁那年,我决意到祖父母的基布兹生活。或许我想通过靠近父亲的父母,来靠近我父亲。
那时基布兹的孩子刚出生就送到婴儿之家,然后到儿童之家。孩子不与父母住在一起。每天晚上父母按时来探望两小时。我在基布兹住在儿童中心。刚到那里时,发现男孩和女孩是一起洗澡的,没有成年人监督。我非常害羞,这对我来说真是太疯狂了!相当可怕的制度。两小时探望时间时,祖父母就来看我。从他们那里,我才听到了一些父亲的故事。
我成年很久以后,开始整理父亲的记忆时,母亲的心也打开了。她给了我一个装满本尼诗稿的手提箱。我开始读父亲的诗。有一首诗,写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纸上。诗名‘博伊特’,日期是1945年,而我是1946年出生的。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爱情诗。我问母亲怎么回事?原来‘博伊特’——意思是明晰,是本尼叫我母亲的爱称。他说自己很冲动,而她非常理智清晰。我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这个名字。
3.边界
父亲被阿拉伯人所杀并没有影响我的世界观。因为我一直就知道他是一个和平的人。我理解这是一起悲剧事件。我母亲也从未对阿拉伯人说过不好的话。她甚至参与过极左报纸《这世界》的活动,是一个非常左翼的人。我从未从母亲、或祖父母那里听到过反阿拉伯人的言论。基布兹的政治环境也是左翼的。我们在基布兹外挖壕沟来防御袭击,同时我们懂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有冲突。犹太人对阿拉伯人做了不好的事,阿拉伯人也对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我们虽历经战争长大,但在基布兹时就已被培养成和平主义者了。
母亲是一个和平的人,她以和平的语言说话,用和平的思维方式思考。她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长大,从童年就饱吸艺术的精华。当她经营察夫塔文化中心时,结识了很多艺术家,举办了许多展览,与艺术家们成为莫逆之交。她从28岁单身到老。她有过一些浪漫关系。我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说因为对我父亲如此深爱,总拿他们与本尼比较。她自己在92岁时开始画画,画了一些美丽有趣、色彩丰富的画作。
男性体内有太多睾酮,喜欢战争,争夺领土和女性。女性生育,而男性将孩子送上死地,这是疯狂。我认为女性之间可以更好地交流,应该主导解决争端。我和一位女性朋友发起组织了“第五个母亲”的活动。我们希望与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建立关系。我们的组织很小,曾给一个村子捐赠了一个儿童玩乐场,带孩子们来特拉维夫的海滩玩。我们并没有感到危险,阿拉伯村民非常友好。但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第二次阿拉伯大起义爆发了。
我们的最后一次活动,是发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献血。我们联系了阿拉伯活动人士,他们在东耶路撒冷献血,我们给‘红大卫星’捐血。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活动,表达我们在乎生命,希望和平,我们有某种血缘关系。参加活动的犹太人比阿拉伯人多。对阿拉伯人来说,参加这类活动可能被视为‘与犹太人合作者’。成为‘合作者’是非常危险的。加入我们的阿拉伯人都非常勇敢。有一位妇女和平组织的成员,来自难民营。她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战争中丧命。我相信每个母亲都希望孩子平安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制止战争。”
博伊特一家都是非常左翼的人。我刚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曾提议我跨过“边界”,去看看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他们反对占领。这次见到他们,刚一落座就问:你怎么看这件事?指的是10月7日的大屠杀。我说:也许这是一次死而重生的机会……
他们说:你这么乐观吗?也许再等一百年……
本尼在诗歌《无边界》里写到:
边界在哪里?
不是一堵墙。
不是一场封锁。
不是一道带刺的铁丝网。
不是那些峰顶耸入云霄的山脉。
不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
只有天边一线依稀封闭了空间,
巨大的环形围栏,围住了唯一真实的领域。
从那里到更远——是另一片土地。
从那里到更远——是一个秘密。
实际上没有人的脚踏过地平线的土地。
它带着距离的秘密,
笼罩在永恒的迷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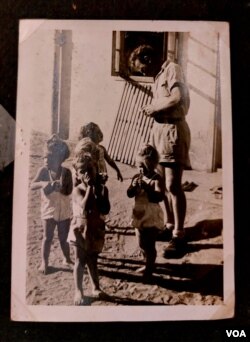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