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頇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稳外资、促内需条文被反间谍法一笔勾销?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寂静。而在这一微妙僵局的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内部脱钩正在悄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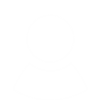
评论区